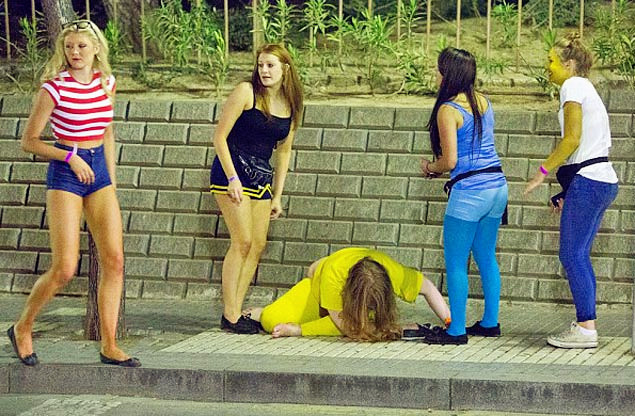张翎:我对中国当下是一个局外人
从票房大卖的国产电影到奥斯卡获奖影片,很多伟大影片都脱胎于经典文学作品。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便是根据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改编而成。张翎作品《死着》尚未出版,影视版权就已授权导演冯小刚。《死着》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3月13日,华裔作家张翎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中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张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著名编剧史航、作家笛安共同讲述逝水流年中的中国故事与人性。
熟悉张翎作品的人都知道,疼痛是她作品中绕不开的主题,有人甚至称她为“疼痛”派作家。张翎新作《流年物语》则不是关于疼痛、关于苦难,而是关于苦难留下的影子。谈到两部新作,张翎戏称自己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写当下小说,《死着》《流年物语》两部小说都做了新的尝试。张翎在《死着》中设计了一个盲人形象——茶妹。她是面对生死问题时唯一的智者,用作者的话说,“既是荒谬的终结者,也是残忍的开启者”。《流年物语》在形式上引入了“物件”(比如手表、钱包、屋檐下筑巢的麻雀等等)作为一个“全知者”,三百六十度视角能够替代单一视角的多重限制。
张翎:从年轻时的中国记忆中汲取创作营养
自1986年始留学,张翎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加拿大,这种写作情景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双面影响。“海外生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毁坏的能力比带给我正面的东西多”,张翎认为,客居海外的一重困难时隔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她与读者市场是阻隔的,对出版市场是阻隔的,无论回来多少次,永远也很难混个脸熟,总体来说是个“过客”;再一重困难是“没有根的感觉”。因为故土已离自身很遥远了,张翎能够汲取文化营养只能是童年。张翎1986年出国,在海外跟海内居住时间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她坦言:“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里,哪一段记忆对他人生产生的印记最深,这才是重要的。”《流年物语》便是汲取了童年、年轻时候故土的记忆,“贫穷”是那个年代的印记。另一方面,这种距离感也并不是全是劣势,“有利的距离制造理性的审美空间”。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与中国当下保持一定距离,张翎反而不会随波逐流,在淡然写作中坚守自己的追求。
陆建德和张翎曾经是复旦大学同学,他还在复旦读书时就听说张翎是温州来的才女,喜欢习作。在他看来,作家笔下的故事背景是哪里并不太重要,这个背景有时候只是一个参照系,或是点缀性的,真正深入读者骨髓的东西才是最为重要的,张翎作品中则具有这种细腻感,对张翎来说,最可贵的经验就是与中国相关。“每个人从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异乡者,离开故土以后对故土有一种洞察”,张翎对故土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使得她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从张翎早年经历和国外生活经历之间一个积极的互动关系,早期的经历是构成她写作得更坚实的经历和基础。“张翎永远是我们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她习惯于反思的,如果没有反思的,然后你就觉得我生在中国必然是如何如何这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文学作品反思会少一些,叙述里面可以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张翎她也不断做这种努力,这种努力使得她跟原始经历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很可贵。”
陆建德:张翎比张爱玲多了一种对阴冷的克服
莫言评价张翎的作品“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受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同为外文系出身,陆建德认为张翎语言的细腻得益于她的英语知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的阅读经验在张翎语言上留下的印记,她有大量比喻都是在单纯的中国女性里面不一定能够写出来。“她跟张爱玲不太一样,张爱玲是很多阴冷的,张翎也有阴冷的部分,如果仅仅有阴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对阴冷的克服。”除了语言之外,陆建德尤其推崇张翎写作中对阴冷的克服。最初阅读《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夜》时,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对生命的阴冷态度,随着阅读的推进,张翎让读者看到他们人性里面更脆弱也是更温暖、更真情一面。每个人讲述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的是对阴冷一种克服,也许他们生活上有不幸的经历,最终他们来回顾那段经历的时候,已经从这个经历里面走出来、超越痛苦。张翎作品中这种对贫穷、对苦难的超越值得回味。
作为当事人,张翎认为自己和张爱玲的区别很大。她说,“张爱玲那种精准描述我是赶不上的,我们仰看世界角度不一样,我们都描述了漫长隧道黑暗,我们两个人不同描述方法,即使我们在描述同一条隧道,我隐隐约约觉得有缺口”。很多人用“锤炼”形容张翎的小说语言,张翎笑称“臣妾冤枉啊”,她的语言和比喻就像雪花一样“飞”到作品中,并没有卖力锤炼。《流年物语》写作时已经开始用减法了,在第二稿删节大量比喻和形容词。
小说改编成电影如同嫁出去的女儿
很多人担心,改编后的《死着》能否将小说的故事情节能否被完全展现出来。关于文学作品改编,张翎认为,“每一个人看小说、看电影,都希望从中得到不同东西丰富这个世界。”小说色调是偏水墨画,偏阴偏冷。电影是偏红偏暖的,没办法比较橘子和苹果。小说她自己认为唯一有自信做好的事,电影是不懂的行当,还是交给懂的人去做。“我写完小说最后一个字,我已经完全切割了,这是我养大的女儿嫁了,接下来事是婆家的事”。
- 张翎:我对中国当下是一个局外人2016-03-14 11:03:01
- “空降”作协当副主席的够格吗?2016-03-10 10:03:07
- 女人为何比男人更容易被说没教养?2016-03-03 10:03:28
- 常听《大悲咒》 善根好佛缘深!2016-02-23 10:02:25
- 奈良美智:在中国问路没人理2016-02-16 10:02:37
- 台湾学者:黑箱子外的政治常识2016-01-27 10:01:04
- 传统令中国人难以做自己?2016-01-25 10: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