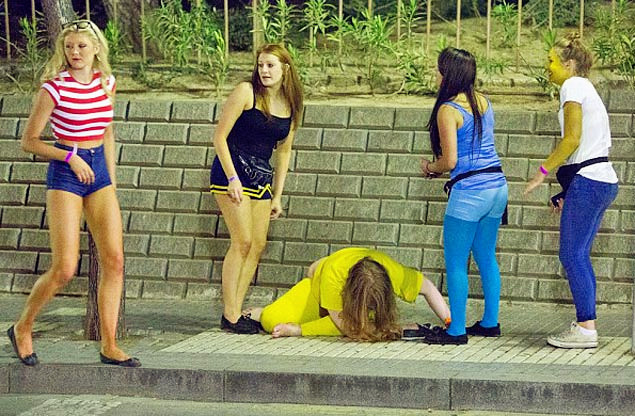解玺璋:致梁启超先生的一封信
任公先生钧鉴:
仰慕先生已经很久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先生离世的八十多年年后,竟有机缘给先生写这封信,只是不知道先生在天堂里能读到否?
第一次被先生的学问文章所打动,是30年前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方汉奇先生是研究中国报刊史的大家,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先生办报,《时务报》创刊时,先生年轻,只有23岁,真可谓“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于是跑到北京图书馆柏林寺报库去查阅(后来才知道北京图书馆最早就是先生创办的),管理员把全套《时务报》抱出来,交给我,是高高的一摞,总有三尺多高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约一百年的“报”,超出我的想像,最初我以为是像今天的报纸一样,没想到竟是一本本“线装书”。
在这里,我用一个学期的课余时间翻阅了总计69期《时务报》,最让我怦然心动的,还是先生的长篇力作《变法通议》。80年代初,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之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候,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犹如长江大河,浪涛汹涌,其势不可阻挡,冲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确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景象,相信您受到这种情势的刺激,也要为之动容的,说不定又要奋笔疾书,为中国的自新和富强做“狮子吼”吧!所以,那时读先生的《变法通议》,自然就有很多共鸣,以为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先生说:“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先生所讲的这些道理,铿锵有力,说的我心里痒痒的,以为把改革、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都说透了。
吾生也晚,无缘直接受教于先生,可谓此生一大遗憾。但心里却始终视自己为先生的私淑弟子,孟子所谓“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心愿,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道德文章无与伦比,岂是我辈可以望其项背的,只能远眺,亦步亦趋而已。这几年,受到几个朋友的鼓动,做了一部先生的传记。不是我妄自菲薄,的确,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是一次冒险,有点不自量力。胡适在其《四十自述》序言中说到,先生曾经答应他要作一部自传的,但由于先生对自己体力精力的自信,一直不肯动笔。然而“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应为五十六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的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
这是说的作先生传记之难。胡适尚且有顾虑,小子难道吃了豹子胆不成?不过,几十年来,前辈学者还是为先生的传记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让我辈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重要的便是《饮冰室合集》和《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订出版。先生病逝后不久,1932年,《饮冰室合集》就由先生的旧友林志钧先生重新编订,并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一版收录的专著和已刊论文、诗词、文稿,较之先生生前编订的各种文集都要丰富,总共由一百四十八卷之多。尽管如此,遗漏的文章、函札、电文仍有很多,近年又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三册出版,弥补了一些不足。这些都是撰写先生传记最基本的材料,先生的文字总是紧跟着时代的,读这些文字,先生进步的足迹则历历在目。丁文江、赵丰田二位先生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作,保存了许多没有经过最后删削的原始材料,都是撰写先生传记最可宝贵的史料。胡适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说到他的期盼:“我们相信这部大书的出版可以鼓励我们的史学者和传记学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我们盼望,这部原料《长编》出版之后不久,就可以有新的、好的《梁启超传记》著作出来。”
现在,胡适去世也有几十年了,他的这番话也说了半个多世纪了,可是,我们至今并没有看到一部配得上先生的好的传记,倒是有许多对于先生的误解和讹传,甚至是诬蔑和谬论。我不敢说自己是什么学者,也不敢说刚刚完成的这部传记就是完美的,但是,我努力写出了我对先生的理解,写出了先生的真性情真精神,写出了先生和朋友们所代表的那个曾经震荡中国知识分子至几十年之久的大运动,以及先生与这个运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实,对我来说,传记的写作倒还其次,真正的收获是几年来系统地阅读了先生的著作,与先生的心贴得更近了,对先生的思想、品性,乃至音容笑貌,更熟悉了,也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以及看问题的方法、角度。最让我感念和受教的,还是先生至老不稍衰的哀时忧国的情怀,先生一生数变,但爱国、救国的赤子之心始终不变,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斯人也,国之元气”,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难得有机会给先生写信,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对先生讲,却不知从何说起。我有时想,如果先生活在当下又会如何?会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先生又将如何面对?可能向当权者提出怎样的建议?我是不相信先生在民族、国家面临最危险的时刻自己躲进书斋去做学问的,先生的学问一定是与民族、国家的进步相关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做这种假设,如果当时的当权者——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袁世凯或段祺瑞——听了先生的意见,历史一定如何如何。我倒觉得,与其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还不如让当下的当权者以及对现状不满的各种势力,都认真地听一听先生的意见,也许倒是有益的。此时此刻,难道还要怀疑先生的诚意与智慧吗?不过,历史有时就是一种宿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中华民族仍有一劫,怕是先生也救不得。不知先生以为然否?晚生玺璋顿首!
- 解玺璋:致梁启超先生的一封信2016-01-18 10:01:28
- 首位为慈禧绘画的西方艺术家:在宫中住了9个月(图)2013-04-14 09:04:26
- 学者举证钱钟书曾痛骂马悦然:仗着中国混饭碗2013-04-14 09:04:26
- 名人身后不安宁:爱因斯坦遭解剖 卓别林遗体被盗2013-04-14 09:04:22
- 江青的所谓“绝命书”:主席你的学生来见你了2013-04-14 09:04:22
- 李鸿章怒斥“鬼子” :倭人委,魑魅魍魉四小鬼2013-04-14 09:04:18
- 张作霖曾说别糊弄老百姓 发行钞票印“天良”二字2013-04-14 09:04:18